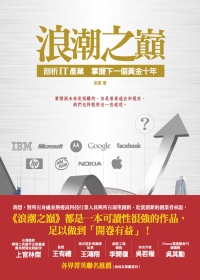這裡指的「大人們」,不是以絕對年齡來論定,而是指抱持「大老或老大心態」的人。他們可能是政府高官、意見領袖、萬事通名嘴,也可能是眾多自以為是者的組合。有些笑罵由人,好官自為之;有些以個人價值觀為唯一準則,據此論斷是非;有些不求甚解卻自吹自擂,以博取虛名;有些刻意顛倒是非,以圖私利。當前台灣充斥著各類消極言論與負向思考,以致民心士氣低落,即令經濟成長率有逼近10%的亮眼表現,也無法打起勁與國同歡。
不論是皇權或民主時代,庶民百姓最依賴的「大人們」就是政府官員,靠他們撥亂反正,靠他們濟弱扶傾,靠他們伸張正義。因此,近日竟有官員宣稱,社會上某些不公不義的亂象,要怪就要怪作亂者而不該怪主管機關,老百姓聞言不免無奈嘆息:「那我們還要政府做什麼?」
有些官員不是沒擔當,也勇於承接前人的爛攤子,但事前未與相關部會充分溝通,就急著提出改革方案,以致漏洞百出,補了西牆又垮東牆,老百姓見狀不免無奈嘆息:「政務運作怎麼變成會這樣?」
本周初在立法院闖關失敗的二代健保方案,就是協調失靈的「代表作」。就衛生署的角度,二代健保旨在防止一代建保的財務黑洞越滾越大,立法進度當然是越快越好。但從全民的角度,比填補一代健保600億虧損更重要的問題是:二代健保改革就能一勞永逸?還是會像美國聯準會(Fed)推量化寬鬆政策(QE)那樣,QE1不夠推QE2,QE2不夠推QE3,然後陷入無止境的紛擾漩渦?綜而觀之,健保改革顯然無法一次到位。
二代健保擴大費基的方式是向有錢人多課稅,因此衛生署原有意改採家戶總所得計算保費,但保費計算標準仍是依據綜所稅資料,而綜所稅稅收有7成來自受薪階級。換言之,在截長補短後,受薪階級還是最大群的「苦主」,仍有大批悠游於地下經濟、資本利得免稅的漏網之魚,繼續啃蝕健保的根基,咬大健保的黑洞。
結果在朝野連日痛批之後,在政院主導下,二代健保保費計算標準昨日出現180度大轉彎,回歸一代健保的「論口計費」,但在經常性薪資之外,另納入資本利得。先不論新版本是否更公平,但如此的朝令夕改,更證明了主管機關先前倉卒提出二代健保原案,只是為了強渡關山,並非深思熟慮之作。
正因為健保改革千頭萬緒,起步更需慎重,如果舊弊未除,新弊叢生,等於走上錯誤的軌道,比不改革還糟。也因為健保改革千頭萬緒,其他部會更不應該抱持著事不關己的態度,否則很難讓人感受到台灣健保已走到馬英九總統所謂「非救不可」的絕境。
政府的「大人們」若真有心要救健保,就要有義無反顧的大決心,各部門齊力矯正既有結構弊端,單靠衛生署補丁式的改革,只能茍延殘喘,無法阻止健保走向破產之路。
相較於好官我自為之,以個人價值觀為唯一準則的「大人們」,多半對自我要求極高,對社會也有相當貢獻,因此當他們義正辭嚴地批判晚輩「這個不對,那個不行」,一般人也很難質疑他們的動機。例如有德高望重的學者疾呼小學生要戒掉漫畫,否則無法進行「思考性閱讀」,又有聖人院長痛斥大學生打工是賤賣自己的黃金時間,都讓人深刻感受到智者的語重心長。
但這兩位「大人」的主張,卻引起不小的反彈,則非言者諄諄,聽者藐藐,實在是時代的變化太快,快到每個世代都應接不暇。不管是長是幼,都必須發揮更大的耐心與同理心,才能體會時代變遷的優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