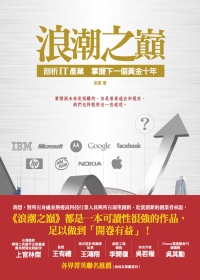台南市政府主持打造鄭成功古商戰船,取名「台灣成功號」,將於明年北航造訪鄭成功出生地日本長崎。
台南市可謂「鄭成功市」,此次造船遠航即是在標榜這個「政治商標」;然而卻也反而凸顯了綠色政治論述的尷尬。此船是仿「戎克船」(葡語,中國帆船)打造,卻稱作「台灣船」;不先就近訪問隔海的鄭成功祖籍福建泉州,卻要先遠赴日本長崎;主辦單位更強調,造船紀念鄭成功,主要是在「加強本土認同/提升主體意識」。但是,談鄭成功,若強調台灣與日本,卻淡化中國,那將是何種面貌的鄭成功?台南市要行銷鄭成功,卻反而凸顯了綠色政治論述的避重就輕、左支右絀。
鄭成功一生人格的核心主題是「反清復明」。南明隆武帝賜其國姓,永曆帝封其為延平王;至其齎志以終,猶痛呼「我無面目見先帝於地下」,抓破面顏而死。日人四方赤良悼曰:「忠義空傳國姓爺,終看韃靼奪中華。」可見,以鄭成功的自許,及國際史家的蓋棺之論,非但皆認其代表「中國」,且是中國的「正統」。康熙併台之後,謂「朱成功明室遺臣,非吾亂臣賊子」;又作楹聯曰:「……敢為東南爭半壁……方知海外有孤忠。」後來,清廷並在台南建延平郡王祠,沈葆禎所題楹聯今日仍刻在正殿:「開萬古未曾有之奇,洪荒留此山川,作遺民世界;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,缺憾還諸天地,是創格完人。」亦即,縱使鄭成功的政敵滿清,也將之視為「創格完人」的中國典範。
在這樣的「大歷史」之下,綠色政治論述卻欲將「中國帆船」改稱「台灣船」,並強調「加強本土認同/提升主體意識」,卻漠視「忠義空傳國姓爺,終看韃靼奪中華」的蓋棺之論;這樣的看法似乎加入了過多的綠色政治顏料,已然篡改了歷史的真相,更扭曲了鄭成功的面貌。
「台灣成功號」下海出航之舉,不啻又引人思考「台灣論述」的出路。台灣是要「去中國化」、「去中華民國化」,一刀兩斷?還是要在「中國」的大概念中,設法創造台灣及中華民國的優勝利基?兩岸關係是要走向鄭成功與清廷兵戎相見的覆轍,還是不同於鄭成功而能創造「和平發展」的機遇?
其實,中共政權也一直十分重視「鄭成功論述」,其中心思想是肯定鄭氏「收復台灣」。江澤民在卸任國家主席及中央軍委會主席時,將一座鄭成功像的瓷雕贈送國務院及軍委會諸領導人,主題是「鄭成功收復台灣」,其用心不言可喻。此外,可能有上千萬人次的台灣人到過廈門,皆曾親見目睹鼓浪嶼的巨大鄭成功石像,握劍東眺,一切盡在不言中。台南市拿鄭成功作文章,有沒有想過要與北京進行作文比賽?
綠色政治論述若要將鄭成功「去中國化」,要將鄭成功「台灣化」,這恐怕反而是自暴其短。其實,以今日的台灣,思考鄭成功「一生無可如何之遇」,不是要切割中國,逃避中國;而是有如前述,要思考如何在「中國」的大概念下創造台灣的優勝利基,更要避免走上鄭成功的覆車之轍。
三百多年前鄭成功時代與今日兩岸情勢大不相同。例如,為了經濟因素,鄭成功不能與中國切割;反而是清廷,實施「遷界令」,將山東至廣東全線沿海廿里的人丁完全撤離,嚴令「寸板不得下海」,完全切斷鄭氏與內陸的經貿關係,成為明鄭覆敗的主因之一。相對以觀,今日兩岸情勢與「清廷/明鄭」的對峙完全相反;非但沒有「寸板不得下海」的遷界令,大陸且成為台灣經貿的主要支撐力。何況,今日兩岸不僅經貿領域不可分割,在人文、社會及政治(如外交空間)的關聯也已難分難割。這與鄭成功欲要兩岸交流而不可得的情勢迥然而異,所以今日兩岸關係的治理與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,皆可與鄭成功時代不同,更不應蹈入鄭氏的覆轍。
台灣的兩岸論述久陷藍綠鬥爭的泥淖中。假設今日台南市由藍營執政,而欲行銷鄭成功;可想綠營必將鄭奚落成「反攻大陸的失敗者」、「寧作中國鬼/不作台灣人」等等;如今綠營行銷鄭成功,卻不惜扭曲歷史,強調「本土性」及「主體性」,不啻又欲套入「去中國化」、「去中華民國化」的綠營兩岸公式。但是,畢竟這艘「台灣成功號」,外形也許肖似當年的戎克船,但已配置了現代引擎及航海儀表,故若以此船來引申闡釋兩岸關係,又豈能不賦以時代觀點,來重建一套綠色兩岸論述?
明鄭與清廷之爭,是兩個專制朝廷孰勝孰敗之爭。但今日兩岸之爭,則是「民主」與「專制」何者符合人性與民意之爭。台灣在經濟領域沒有「去中國化」的條件(明鄭因在經濟上「被去中國化」而覆敗),但台灣在體制的領域上,卻有在「中國」的大概念下,爭取在文明、文化、人性、民族、民生及民主上的優勝地位之條件。去中國化(或被去中國化)是明鄭覆敗的主因,台灣的生路則應在「中國」的大概念下尋求優勝。
把鄭成功變成「台灣人」,並無法建立綠色政治論述;正如無法把媽祖變成「台灣人」。紀念鄭成功,反而是要思考,在沒有可能「去中國化」、「去中華民國化」的大情勢下,如何為台灣爭取在「中國」這個大概念中的優勝地位與生機活路。
當「台灣成功號」訪問廈門或泉州之日,兩岸皆應思考,必須超越鄭成功時代,不要踏上三百多年前的覆轍。
【2010/12/07 聯合報】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